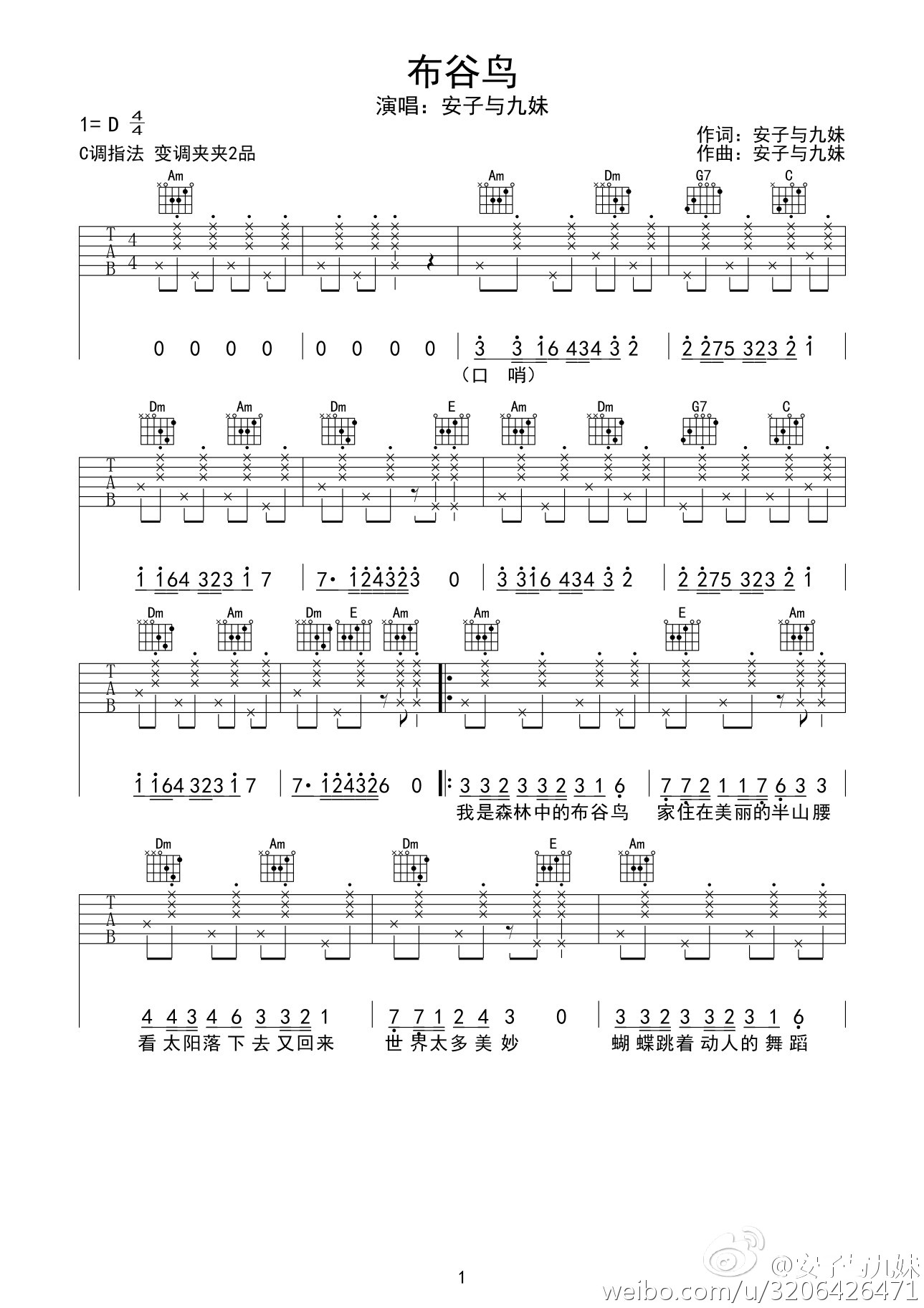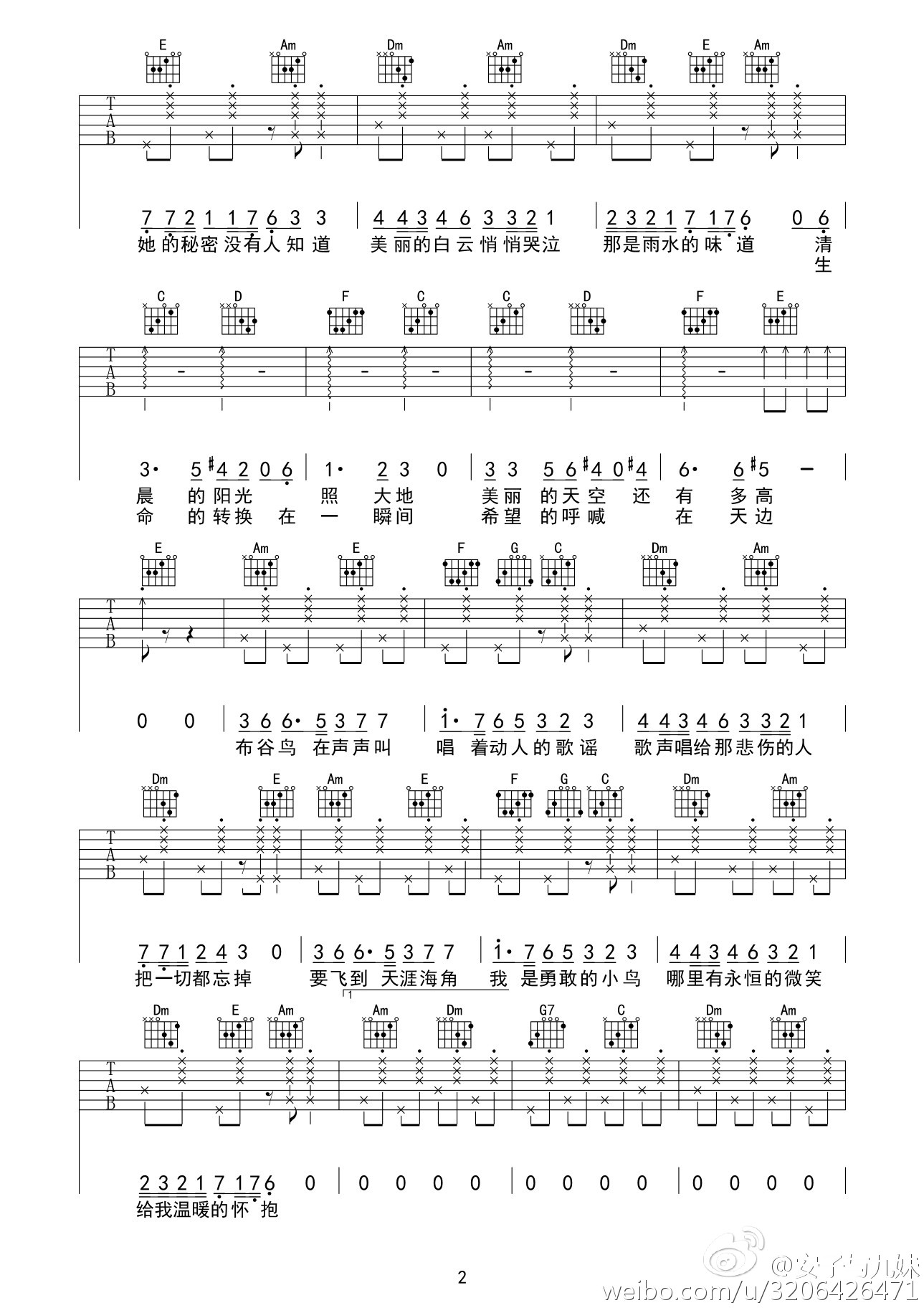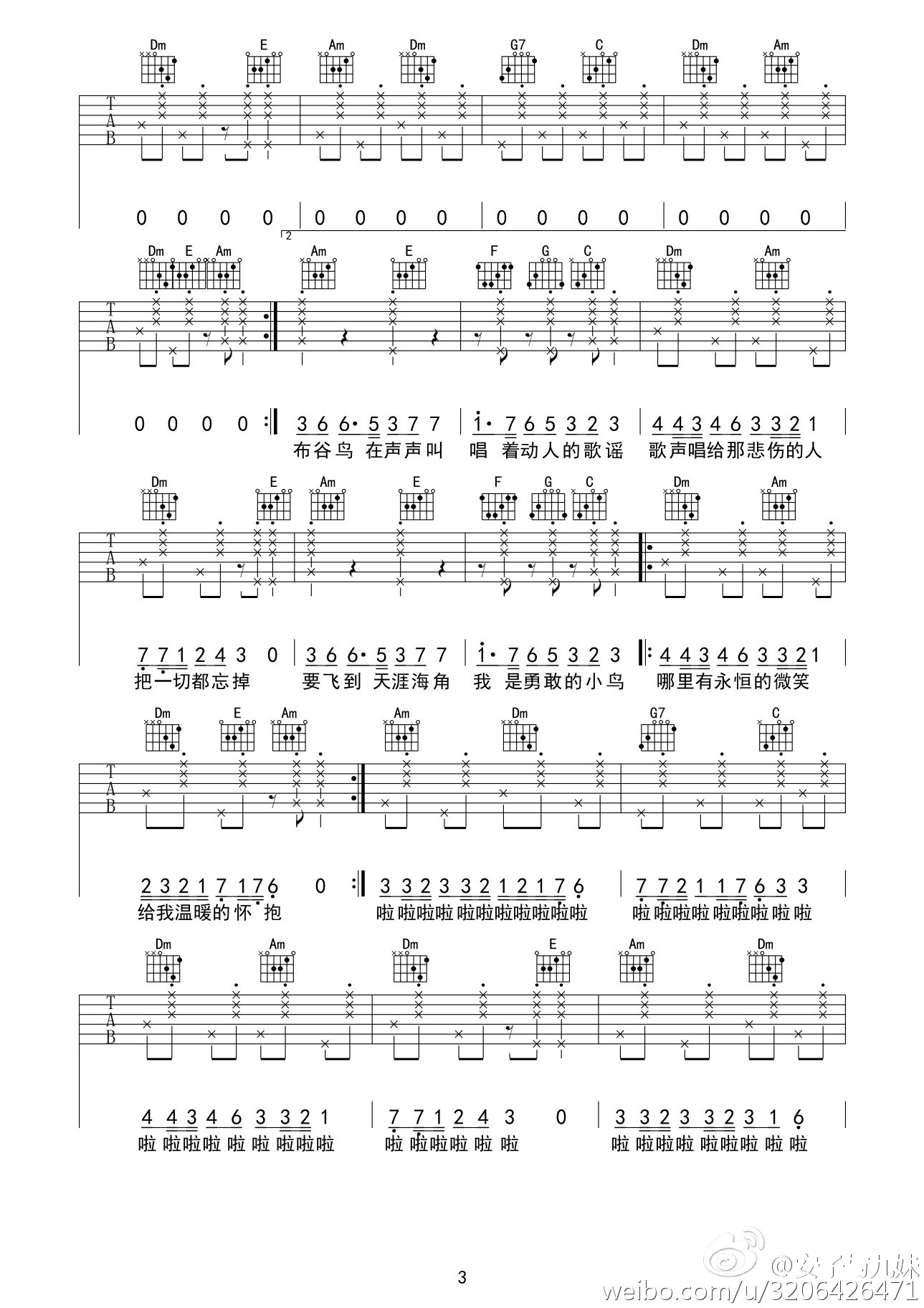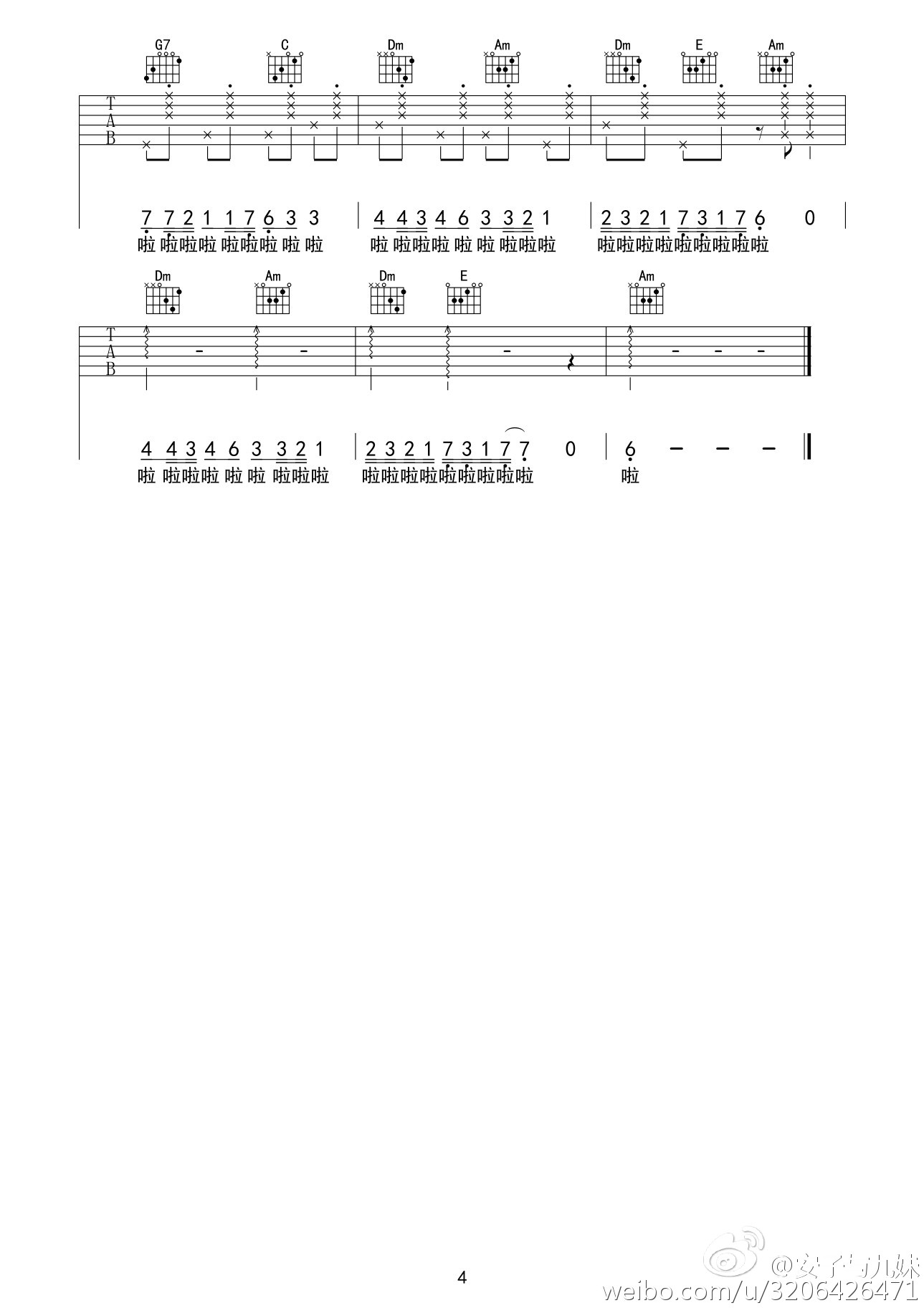《布谷鸟》以自然意象为载体,通过布谷鸟的周期性鸣叫构建起时间流逝的隐喻体系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四声一度"不仅是鸟类学特征的准确捕捉,更暗合农耕文明对季节轮回的原始认知,这种生物节律与人类生命节奏形成微妙共振。羽毛与鸣声的意象群构成双重符号系统:既指向候鸟迁徙带来的时空错位感,又隐喻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漂泊状态。歌词中"麦穗低头"与"空山新雨"的并置,将农业社会的集体记忆与当代个体的孤独体验焊接在一起,形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张力。布谷鸟作为自然信使的角色被赋予哲学意味,其鸣叫既是生命提醒也是存在拷问,在机械复沓的节奏中暗藏存在主义式的诘问。农耕文明的集体无意识通过鸟鸣声获得现代转译,那些被混凝土森林割裂的时空记忆,在声波震荡中重新拼合成连续的精神图谱。歌词通过对自然物候的诗化记录,完成对现代性时间异化的温柔抵抗,在电子化生存的缝隙里植入草木生长的原始密码。这种将生态智慧转化为抒情话语的尝试,最终指向的是人类与自然重新缔结永恒契约的可能性。